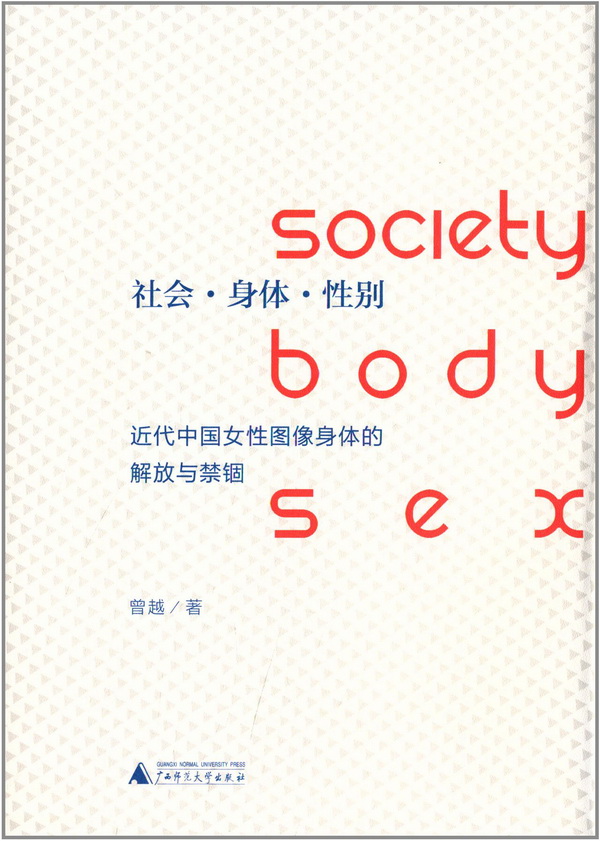我们可以从《延禧攻略》中的一幕情节开始:年将半百的乾隆继后那拉氏对着镜子检查自己脸上的皱纹,并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保住容颜。为此产生的焦虑、疑神疑鬼以及恐慌最终让她失去之前的冷静与步步为营,而导致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奴才所利用,另一方面与乾隆关系江河日下,最终发生断发一事。编剧为那拉氏最后的失算所安排的导火索便是她的容颜问题。而预设的前提则是,年轻姣好的容貌在后宫这样一个地方占据着十分重要甚至核心的地位,而它往往直接决定皇帝是否会宠幸。这是后宫剧对于中国传统帝制下皇城后宫女性的想象,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如一面镜子般折射出一个悠久的关于外形的迷思,即——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外形总是能够与地位和权益相连接的,而由此获得相应的报酬。
传统中国中的女性最主要为“三从四德”这一来自儒家的教诲约束和塑造着。“三从”来自《仪礼》,“四德”出自《周礼》,即所谓的“德言容功”四项。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发便会发现,在传统礼教对于女性的要求中,妇德与妇言都在妇容之前。对于注重伦理道德的儒教而言,这是可想而知的。而即使是妇容,其所主要强调的也并非我们如今所以为的关于女性的容貌外形,它更多强调的是女性的某种行为表现,即需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能轻浮随便”。纵观儒家教诲,我们似乎很难看到有直接对于容貌外形作出具体要求的,它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体现女性端正的品德与恰当的言行修养。 因此,当我们如今看到后宫剧中,嫔妃们为了自己的容貌外形而大打出手时,与其说它是帝制儒教对于女性压制的遗毒,更合适的说法或许是现代人自身对于(女性)外形的迷思所造成的唐突古人。对帝制儒教中的女性而言,她们随着处于家族中角色的改变而被要求展现出相应的行为规范。她们更像是对于一个已经有了根深蒂固涵义的位置的暂时占据,两者比较,她们是客,这个角色与位置是主。所以在《延禧攻略》中,富察皇后去世后,需要另一个妃嫔来占据皇后之位。而“皇后”这一角色无论谁来扮演,最终都得符合它已经被设定的形象。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下,传统中国女性的外形或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如我们在后宫剧中所看到的那般重要。 就如米尔斯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外形是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诸多变量相斗争与协商所产生的结果。在以儒家道德伦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帝制中国,达到彬彬典范的是“文质”融洽,而非外形的俊朗或美丽(在庄子笔下,我们看到真正悟得大道的往往是那些身残体缺的畸零人;而庄子对姑射神人肌肤与动作的描写,同样是为了凸显出其内在的“神人”特质)。因此,对女性而言,完美的品德修养是第一位,而非外形。而一旦对于后者的关注超过前者,就可能遭到批评与打压。我们从历代正史、野史以及传说故事中时常看到的对于“红颜祸水”的描述中,对容貌外形的妖冶与非主流的强调总是占据大半篇幅。而自元明以下所产生的烈女传统中,一些女性为了表明自己的贞洁而时常有意破坏自身的容貌,以此凸显出内在品德的高尚。 就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在外形与品德之间,胜利的总被预设为后者。占据正统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使其拥有强势的权力来压制和铲除那些过分迷恋外形而忽略了道德修养之异己。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我们对这句话稍作改变,也不正是我们所讨论的外形与道德的关系吗?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美好的外形同样并非仅仅一张皮相而已,无论东方西方的传统中所出现的面相学都表明了这一点,即在古人看来,外形与一个人的天性或品质有着直接联系,透过观察一个人的五官,便能判断出与ta有关的一系列事情,从过去到当下,甚至还能预测未来。面相学于中国最早出自《礼记》(如“凡视上于面则傲, 下于带则忧,倾则奸。”),在东汉末年至魏晋,面相学在中国颇为风行,甚至还出现了许多相关著作;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其后一直流传,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还有一节专门讨论面相学。在19世纪,它被认定为伪科学,才渐渐衰败。在中国我们却时常依旧能在民间街头巷尾看到以看面相为生之人。 20世纪初期西方第一次使用真人模特时,设计师指出好的模特的标志就是拥有“瞬息的特质”(ephemeral quality),而这一特质似乎来源于精神。米尔斯指出,这里的“特质”指的其实就是模特的外形。延续着古老的面相学思想,外形与精神之间的某种镜像式的联系依旧未在现代社会中彻底断绝。而这一观念蔓延至今,当我们评判一个人外形如何时,我们往往也就连同调用了一系列于历史中所形成的与之连接在一起的关于“内在”(精神)的判断。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个始终若隐若现的真相,即于历史与社会文化中所建构出的外形中蕴含着鲜明的权力轨迹。米尔斯指出,“模特的‘外形’是社会不平等的视觉体现……外形是权力表现的象征,是性别、种族、性取向和阶层的交接点,是我们想象中的社会差异和幻想的视觉表现。”
随着近代中国对于帝制以及礼教伦理的批判与攻击,借助西方思想,现代中国知识阶层开始建构一系列新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来取代陈旧的传统。在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以国族复兴为旗帜的呼唤下,传统被困于“内”、困于“后”以及困于小脚的女性开始走出闺阁,一方面根据西方个人主义建构出新的自我主体,另一方面则在国族的要求下开始强身健体,为国为民。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或对立,它们时常融于一体。传统道德规训依旧流传于社会之中,但其约束力也已日薄西山,而在新道德还未完全建立中,女性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形象。天足、天乳、女性裸体以及新式女装都在这一潮流下激荡澎湃。 在曾越研究民国女性解放的专著《社会·身体·性别》中,她指出,在关于女性与社会的互动中曾出现过典型形象的转变,即从前期象征着新生、希望和觉醒的女学生形象转变成后期商业大都市中的摩登女郎形象,后者被塑造成一群迷恋华服、注重容貌与生活享乐的女性,对民族国家的危亡意识淡薄。这些摩登女性在之后的左翼文学以及意识形态叙述中被称作“小资产阶级”。 这些“小资产阶级”女性实则是女性解放中必然会出现的正常现象,即女性关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喜好与欲望,关注她们穿在身上的衣服以及自己的外形。虽然其中掺杂着消费主义的阴影,但无论如何它依旧有利于女性的进一步解放。但这一解放最终随着左翼的批判以及其后国家陷入外敌入侵的漫长战争中,而渐渐消弭。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新的关于两性形象的意识形态。民国大都市摩登女郎成为“资产阶级堕落”的证据,新的女性形象被建构。戴锦华老师在其《性别中国》一书中指出,新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随之重新确立起的父权文化中被“去性别化”。“男性与女性间的性别对立差异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代之以人物和故事情境中阶级与政治上的对立和差异”。而“劳动妇女的形象”也开始取代了“那个不断被重述和移植的‘娜拉’……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形象”。而无论是革命女性还是劳动妇女,她们在其公共形象展现中往往千人一面。在此,曾经一度浮出历史地表的对于外形与容貌的关注再次淡出,而对于革命与阶级的忠诚成为对于女性新的政治与道德要求。 在这个女性“去性化”(实则是“男性化”)的时代,“女性特质”更是自绝于劳动阶级的资产阶级反动。能顶半边天的女性最后成了“非女性”,从内到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会出现1980年代李小江等学者以及诸如张洁、宗璞等女作家对“女性”的重新寻找。李小江老师于1980年代末出版的《性沟》指出的便是存在于男女两性于历史中不同步地发展所产生的性沟,在当下不但未能填平,反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来。李老师对于“夏娃”的呼唤,对于女性所作的本质论的建构都是面对1980年代前主流性别意识形态所作的批判与反抗,希望从中把女性重新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接续了20世纪初的女性解放。但这一对于“女性”的呼唤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因此刚从“去性化”/“男性化”中走出来的女性便立刻被抛到资本与消费所带起的大潮之中,而再次面对新的困境。 这里的困境在20世纪初的女性解放中便已经出现,重新解放的女性走入资本与市场,开始新一轮的被利用、消费和搏杀。这一状况延续至今。在现代中国崛起的庞大市场以及消费大潮中,新的外形观念被建构,而与之共生同构的则是新的性别/性别气质意识形态。就如米尔斯指出的,“外形是一面社会不平等的镜子,是权力的表象”,透过它,我们看到外形这张“皮”背后的“春秋”。 |
相关资讯
- 敦煌文书里的婚姻与家庭(2018-10-09)
- 当我们在讨论“真正的男人”时,其实在塑造“真正的女人”(2018-09-20)
- “像个女孩一样”:谈谈我们周围充斥的性别化词语(2018-09-16)
- 机洗内裤容易得暗病?这个锅我们袜子不背!(2018-09-14)
- 对于《罗马》,我们持保留意见 | 威尼斯(2018-08-31)
- 作为“哺乳类动物”,我们对乳房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2018-08-27)